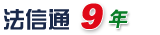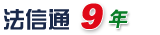证明标准问题之司法实务考查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4日
来源:琼海刑事律师 http://www.qhxshls.com/
一、证明标准问题在司法实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在笔者调查的134个案件中,涉及需要在分析、判断若干个证据证明力基础上综合对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程度作出评价和判断的就有121件,占90.3%。其中刑事案件占98.3%,即60个刑事案件中只有1件由于证据过于充分,法官对其是否达到认定案件事实的程度未加任何评价;民事案件占81%,即63件案件中有12件或者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事实完全无争议,或者由于当事人自认和法官推定,不需要再对证据及证明程度作分析和判断;行政案件则是百分之百的进行了证据及证明程度的评判。还有一级调查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笔者所在的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两年间讨论的379件个案中,就有308件研究讨论的重点是分析所收集的全部证据能否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问题,占讨论案件数的81.3%;而该中院所辖的20个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两年间讨论的与证明标准问题密切相关的案件事实的平均案件数占讨论个案总数的 36.2%,其中最高的为100%,即每个案件都是在讨论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再讨论法律问题,最低的也占18.7%。上述调查结论足以充分表明证明标准问题在法官和法院断案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证明程度和证明标准的评判工作,审判工作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基础,成了空中楼阁。
二、立法标准与实践标准之间有很大距离
我国三大诉讼法中都有与证明标准问题有关的条文,“‘虽然条文字面上有些差异,但一般都将其概括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根据刑诉法第42 条;民诉法第63条和行诉法第31条相关规定,”事实“指的应当是”客观事实“。因而正像很多学者所说一样,我国三大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并且追求的都是客观真实。不过,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则不那么简单。首先是三大诉讼之间有差别,而且认定事实都不可能全部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调查的情况看,可以说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体现得较为充分。在调查的57个有罪判决的刑事案件中,法官在判决书中判定属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和犯罪基本事实清楚,足以认定的有34件,占59.6%;在9个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案件中,被法官判定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有6件,占66.7%。而63件民事案件中,法官判定属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或者事实基本清楚,足以认定的则只有22件,占34.9%。这就可以看出同样是认定了案件事实,但不是都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要求,且刑事、行政和民事法官把握的证明标准是不一样的,特别反映在达到法律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数量和比例上有很大的差距。其次是每类诉讼中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刑事有罪案件除59.6%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外,尚有33.3%或者是证据基本能够印证和采信,法官比较勉强地认定案件事实,或者是间接证据基本能够形成锁链,犯罪事实可以认定,或者是因证明力较弱而降格处理,还有个别严格说是基于不相关因素降低了最低证明要求而将”疑罪“认定为犯罪。行政维持案件中有2件占22.2%的案件,法官认为认定事实只是有相应的证据或者只是根据证据确认事实,并不能达到”清楚和充分、确凿“的程度。民事案件情况就更不一样了,除上述达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外,以下几种情况法官也认定了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一是根据证据基本可以确信的(7件,占11.1%);二是双方当事人对事实没有争议的(7件,占11.1%);三是间接证据基本能够形成锁链的(2件,占3.2%);四是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方举证不足的(23件,占36.5%);五是法官推定事实存在的(1件,占1.6%)。
根据上述情况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三大诉讼基本统一的法定证明标准与实践中掌握的情况距离是比较大的,说明立法并不符合实际,或者说司法实务无法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第二,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实际上是最高证明标准而非证明标准原本意义上的最低证明标准。这说明刑诉法第163条、民诉法第 154条和行诉法第54条以及相关规定虽然与证明标准问题有关,但其实并不是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准确说应该叫证明要求(即最高证明标准)。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并无证明标准的立法;第三,法院和法官在证明标准的掌握上并非刑、民、经、行都必须追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同一的证明标准,实际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既体现了不同诉讼的不同特点,也是实际情况,说明了人的认知的有限性,而非立法那样理想化。
三、法官把握证明标准尚处于非理性和低层次状态
在国外,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制定法条文并不直接涉及证明标准问题,但法官在实践中对此有很深的研究和广泛运用,而且还通过判例法或判例形成了一些便于操作的等级和量化标准。而在我国的情况如何呢?笔者分别就所调查案件中法官对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达到的证明程度的判断结论进行了梳理。从高到低,从强到弱大致有以下典型的表述方式:1.证据非常充分完全没有疑问的,在裁判文书中铿锵有力地表述为“证据确实(确凿)、充分”,这在刑事和行政案件中使用最多;2.证据虽然也很充分但法官认为尚未达到确凿无疑程度的(如被告否认但其他证据充分),表述为“足以认定”,这在刑事案件中使用较多;3.证明标准不是很高但也达到了认定事实程度的,不作主观评价而客观叙述为“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4.证据相对较弱但法官认为也能够认定事实的,表述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或互有联系),形成锁链,对事实予以认定”,这在以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使用较多;5.在难以查明真实事实时推定一方主张的事实成立并表述为对方“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否认或说明理由,故对一方证据采纳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种情况在刑事案件被告人翻供但又无充分理由和民事案件对方依据不足情况下使用较多;6.双方证据相互矛盾无法排除,法官经取舍作出判断的,表述为“证据间产生的对抗和矛盾不能排除,故事实不能认定”,这多在“一对一”的证据和双方证据冲突,法官有疑问的情况下出现;7.虽有一些证据但法官认为,对认定事实没有把握的表述为“不足以推翻(或不足以认定)”;8.明显证据不足的表述为“证据不足(或依据不充分),事实不能认定。”上述前5种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表述;后3种则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未达证明标准的表述。
上述可见,我国法官虽然不像国外法官那样对证明标准问题非常有意识和有研究,而且有一套比较系统而精确的操作方法,但还是在区别不同的证明程度,而且也尽可能地在用比较准确的语言来表述自己对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程度的判定,以及由此作出的证据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结论,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也可以看出中外法官司法实践中的相通之处。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判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化的认识和运作。第一,对这种自然形成的证明程度的等级并没有有意识地进行思考、总结和研究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形成大体一致的把握标准,而是法官各自凭经验判断掌握,随意性很大,证明程度的表述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第二,最终作出的判断结论与个证证明力的分析结论有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个别法官那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成了一种千篇一律的套话草率使用,而不管本案证据是否达到了这一证明程度以及实际上究竟能证明到何种程度。在调查的案件中就有1个案件,在证据明显有疑问的情况下法官仍然作出了“证据确实、充分”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其前面的个证分析完全不一致。第三,对证明程度和证明标准缺乏精确和量化的标准、方式,基本上没有证明程度的等级和“盖然率”的概念,而是一种“估堆式”的笼统判断,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方法。
四、证明标准与单个证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每个证据都要对案件事实起不同程度的证明作用,而证明标准是在对单个证据证明作用分别分析认定的基础上,对在案全部证据是否能够达到认定案件事实的最低限度的证明要求的综合判断。可见,证明标准的判断和个证证明作用的判断既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又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从调查情况来看,这种联系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证明标准与证据数量有一定联系
以44个被调查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为例,每个案件的平均证据数为 12.75个,10个以上的有26件,占59.1%,最多的达到44个,最少的只有2个。其中刑事案件个案平均证据数量又多于民事案件,前者为14.24 个,后者为9.87个。这一方面表明证据的数量是达到证明标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和因素,但同时也表明二者并不成正比例关系,即不是证据越多证明标准就越高,证据越少证明标准就越低。虽然从上述数据看,大多数情况下证据数量与达到证明标准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尽然,因为有5个案件,从证据数量说就有8个到17个之多,但却都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被法官判定证明的事实不成立;而只有2个证据的一个民事案件和4个证据的一个刑事案件则绝对是达到了证明标准。因此可以说,证据数量虽与证明标准密切相关,但绝不能得出其对认定事实起决定作用的结论。
(二)证明标准与个证的证明力大小有实质性的联系
调查结果显示,第一,80%左右的案件是否达到证明标准,书证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明力较强的证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一个名誉权纠纷案件中,证人袁某某多次(包括在法庭宣誓作证)证明原告领取奖金的事实存在,但笔迹鉴定结论是奖金发放表上的签名不是原告亲笔。法官据此认定,在两种证据内容发生冲突时,法院采信鉴定结论,认定原告没有签字领钱,因为鉴定结论的证明力高于证人证言。在另一个刑事伤害案件中,被告人辩称被害人眼部受伤系跌倒而非自己加害所致,但法官根据被害人眼部伤系挫伤的鉴定结论,认定被告人辩解不成立。第二,法官主动调查收集的证据对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所起的作用也比较大。在调查的案件中,虽只有5件案件法官主动调查取证,但其证明力都得到了确认。如一起民事离婚案件,法官主动调查了3个关键证据,虽双方对这3个证据存在不同异议,但法官认为他们均未对异议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否认或说明,所以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述可见,单个证据的可信性越高就越容易达到证明标准,因为这越容易使法官相信其证明的事实是真实的。换句话说,证明标准实际上依证据可信的价值而定,而与证据数量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三)证明标准与个证和事实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个证相互印证情况以及个证之间的联系紧密相关在调查案件中,有相当部分案件并不能以少数证明力强的证据直接认定案件事实,而是对若干证明力相对弱的证据综合分析后决定其是否达到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这种情况最为典型的是连续犯罪(盗窃、贿赂等)的认定。调查中有两个10 次以上连续盗窃或抢夺的案件,虽然每一次犯罪的证据都只有从1个到8个不等的被害人陈述或买赃人的证明,如分开来看似乎每一次的证据都难以达到证明标准,但法官将多次作案的被害人陈述等证据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后,判定案件达到了证明标准,因而认定被告人有罪。另外,案件证据多为证人证言情况下,证言之间相互印证情况及其与事实关联程度、证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证人与本案的利害关系等,都对是否达到证明标准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方面的案例非常多。
综上,在审判工作中,个证的认证固然重要,但是证明标准的判断更是比较复杂和同等的重要,而且二者之间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从实践来看,如果说我们对单个证据的认证需要给予也确实给予了充分重视的话,那我们对证明标准问题却关注和研究得非常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和需要立法、理论和实务界努力填补的空白。
五、证明标准的判断有时带有较浓厚的主观色彩
从概念上说,证明标准是以客观的各种资料和信息为基础对事实认定与否划定的统一标准,因而尽管它是一种主观判断,但也应当具有相对确定的客观标准,这一点相关调查结论可足以说明。在调查的134件案件中,有85%左右的案件并不存在证明标准判断的争议,即只要具备一般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的法官,根据查明的相同证据,对事实的认定与否自然会作出同样的判断。这类案件中,法官在认定事实上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明显。但是,调查结论也同样显示,这种客观标准在部分案件中似乎只具有参考的价值,而法官的主观性和自由裁量因素对证明标准的判断起着制衡和关键的作用。134件案件中有15件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个问题。这15个案件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在案证据是否达到证明标准不明显,或者说认定事实明显有疑问的情况下,法官认定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认定事实成立这种案件有4件,比如一刑事伤害案件,查明的证据只有被告人庭前的供述、一个证人提供的传来证据和与被告人供述行刺部位大体一致的伤情鉴定结论,而法庭上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另有他人行凶。对此法官认为:被告人构成伤害犯罪,其另有他人作案的辩解无相应的证据佐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还有一个案件,法官在判断证明标准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即在检察机关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主观认为被告人的辩解无相应证据,因而认定了起诉的事实。这里法官的证明标准似乎出了问题(刑事案件采用了民事案件采用的较低的优势证据标准),因而这种主观认识的正确性要受到很大质疑。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达到证明标准有疑问的案件中,笔者并未发现法官因此而不认定相关事实的情况,包括刑事和民事案件。这可能也反映出中国法官特有的思维模式。
(二)对大体相同的情况,不同的法官作出了不同的判断
这种情况有5件。其中有4件是在双方证据相对应和矛盾情况下,法官主观起决定性作用作出选择。比如在厂受贿案中,被告人及其子的供述和证言与另两个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的证言形成了“一对一”的矛盾对应关系。法官最后认为:在无其他旁证支持的情况下,指控证据间产生的矛盾和对抗不能排除,被告人受贿事实不能认定。另一毒品案的情况是:在认定被告人购买毒品是否知情时,法官在被告人不承认知情和同案人证实其知情的相互对应的证据中选择了后者,故而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在一个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中,面对技监局对石料数量的丈量认定书和被告提供的自己对石料的盘点丈量记录两份证明石料数量不相同的证据,法官经分析认为技监局认定书可信度大一些,故按此证明的内容认定相关事实。还有1件是在证据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一审法官认为认定担保关系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判决被告承担担保责任,而二审法官则认为认定被告承担担保责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而撤销了一审判决。
(三)采用事实推定方法自由裁量证明标准达到与否
这种案件有3件。一个案件在确定丁某系游泳中溺死还是游泳时因心血管疾病发作而猝死时,结合不能明确认定的鉴定结论和其他相应证据,法官认为:应依一般社会经验和常识水平来判断。本案尸检发现丁某患有心脏慢性缺血性改变,本人又系在运动之后跳入水中,以上条件的成就完全可能引起死亡的后果,故丁某溺死只是表面现象,其死亡的实质原因是心血管病猝死。在另一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肇事者出车是因公还是因私这一关键事实的认定,由于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法官分析了所有证据后认为:死者与肇事司机均为某商场职员,因死者生前就以个人名义同某服务部(肇事车准备去的地方)做电脑业务并被商场处理过,所以从常理和情理上分析,商场就不可能派车送死者去从事个人业务。故确认肇事行为系非职务行为。一个刑事案件中,在被告人谭某运送、销赃被盗物资是否与其他被告人事前有通谋的问题上证据不充分,法官以行业习惯等4个相关事实为据推定谭某等人事前有共谋,系共同盗窃。在上述案件中,可以说证明相关事实成立的证明标准都未达到,但法官借助事实推定并运用自由裁量权认定相应事实成立。这之中法官的主观因素体现得非常充分。
法官在证明标准问题上主观因素所起的作用,一方面表明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上同样存在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自由裁量权与适用法律上的自由裁量权相比应当说要小得多,因为证据是否达到证明标准在大多数案件中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些案件中法官认定事实不能有任意性而必须受到职业群体共同认识水平等因素的拘束和规范,否则裁判制度的统一性将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主观色彩在处理疑难案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和填补作用。再一方面也使我们意识到,应当认真研究法官如何正确行使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的自由裁量权,以尽量避免出现主观擅断。
六、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一般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但并不绝对
说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一般高于民事案件是基于以下情况:
一是调查结果显示,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较高证明要求的案件和达到能够认定案件事实起码证明标准的案件数相比,刑事案件占59.6%,行政案件占 66.7%,民事案件则只占34.9%。也就是说,大多数民事案件的证明程度与刑事和行政案件相比要低。二是当出现控辩(诉辩)双方证据相互对应和矛盾时法官的思路是不太一样的。刑事案件一般是从内心确信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合理怀疑和能否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证据“一对一”或双方证据大体相当情况下一般不认定犯罪事实存在;而民事案件法官一般是对双方证据进行掂量,哪方证据更为可信和分量更重就倾向于认定哪方主张的事实。前述法官对受贿事实的不认定和按技监局丈量认定书认定石材数量的案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案件。这个案件证据所能够证明的事实是:原告之夫和子在服用从王某某中药店抓的治疗癫痫病的中药后相继死亡。经化验,该药中含有致命的“毒鼠强”。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终结后,认为中药中的“毒鼠强”的来源无法查明,故追究王的刑事责任证据不足。但在其后进行的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中,法官认为虽然王某某负刑事责任的证据不足,但原告之夫和子死亡系从王某某处所抓中药中所含“毒鼠强”所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故王某某有过错,应负不可,推卸的民事赔偿责任。此案颇类似于美国的辛普森案件,可以算得上是我国审判实践中把握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高于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并不绝对。被调查案件中有两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个结论:一是法官对某些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把握并不比刑事案件低。在一起因障碍物引起的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事实认定中,法官判定:高速公路管理处虽举证证明已按路政管理制度履行巡查义务,但由于该高速公路的现代化条件足以保证管理处对路面异常情况能够及时发现并清除,而管理处却没有及时发现和清除,证明其没有尽到勤勉而谨慎的高度注意的义务,所以应当承担责任。还有一起存款纠纷案,原告诉称在被告处办理了25万元的存款业务并提供了存款凭证,而被告则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原告只交了23万现金的录象资料。此案如果采用盖然率在75%左右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被告可能因其证据的证明力略大于原告证据的证明力而胜诉。但法官认为,被告要推翻自己出具给原告的存款凭证必须要有充分和更为有力的证据,而录像资料却尚未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判决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在这两个案件中,法官采用的证明标准显然很高,如果要用百分比来估量和比喻这个标准,我认为起码在95%以上。这种涉及高度危险作业和公益性的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几乎是刑事案件采用的“无疑确信”或“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思路我们在有关介绍美国司法实践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二是刑事案件中存在“罪疑从轻”的现象。调查的案件中有3起恶性杀人案件,因为多个证据综合起来法官仍然认为证据比较“软”,但似乎又比“存疑无罪”的证明程度高而不能判无罪,法官在“两难”情况下不得不选择降格判处。?对我国刑事审判中这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一位在中国讲学的美国法官针对一起类似典型案件给我们的解释是:法官(指中国法官)的判决并无不当(该案为强奸杀人后分尸,罪犯被判无期徒刑),因为适用无期徒刑的证明标准要低于适用死刑的证明标准。对这种解释我们现有的理论难以自圆,而且似乎学者也感到茫然。其实它的关键问题是对本未达到但又接近证明标准的案件降格处理。我们在谷口平安介绍的日本司法实践中隐约可以看到类似的裁判思路,只不过谷口平安指的这种“比例认定”方法出现在法官认定民事案件而非刑事案件中。如果刑事案件因证据欠缺而降格处理,这似乎与“罪疑从无”的无罪推定原则不相一致。
在得出本问题的调查结论时,笔者感到异常的惊奇。因为在上述特殊案件和特殊情况下,中国法官无论是把握其证明标准的总体思路,还是对具体案件的认定方法,都与国外法官的相关司法实践不谋而合,有的典型案件还惊人地相似。这说明国内外司法实践遇到的问题有相似的地方,法官对案件的处理也有其共同性,中国法官的司法实践也不乏有先进理念的闪光。但遗撼的是我们的立法和理论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实践,很少有人对这方面问题进行过系统的总结和研究,立法上更为滞后。以至于一些处于朦胧状态的进步的司法理念得不到发现、提升和肯定;而有些作法又很少有人去研究和论证,这又导致理论和立法不能很好地指导和规范实践。